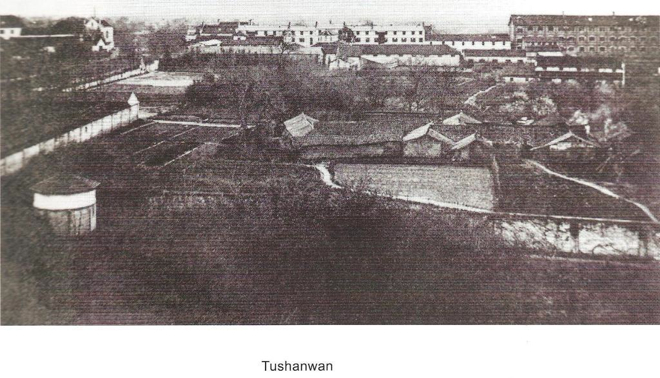为了迎接世界博览会,今年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艺术项目如洪水猛兽一般向上海袭来。其中一些很棒,一些过分夸大,而另外一些则出现在真空地带——一个以世博会为由、超出上海艺术圈可见(和可想)范围的黑洞。谁不是仍然在拒绝来自人们的邀请,去看这样或者那样设计拙劣的世博会项目的?
暂且不谈质量,在历史上中国从来也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到过如此众多的外国艺术项目;鉴于此,(目前)似乎正合适探讨西方艺术进入中国的历史。这一对话跨越了数个世纪,涵盖了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动机,从商业的、到意识形态的、到纯艺术的(目的)。
西方艺术进入中国的知识,通过了各种不同的渠道,包括耶稣会神父、中国人开办的学校、日本艺术老师、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美术书籍、来自大陆和台湾的杂志、回国留学生、展览以及通过和西方艺术家有限的交流。由于所有信息的筛选和波动的政治气候,中国的现代艺术史并不单单是加入“时间间隔”于其间的西方艺术史的反射;而是玩笑似的对待不同的西方运动,接着又放弃了,接着又玩笑似的对待其他的运动,结果却回到了从前的运动。同时,还有持续不断的平行的国画(中国水墨画)历史,它仍然在不断地对中国现代艺术家产生着影响。
在此,我将试图追溯西方影响力的足迹,以审视那些涉及到的参与者,和自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80年代他们是采用怎样的方式把西方艺术的意识传入中国的。在接下来的《燃点》第三期的第二篇文章中,我将会探讨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当前,对中国先锋派产生影响的艺术家和理论家。(1)
利玛窦(Matteo Ricci)和耶稣会(Jesuit)的影响
中国与西方绘画的第一次接触当然乘载了宗教和政治动机。但是,无论如何耶稣会获得了向中国介绍媒介的荣誉。
第一幅进入中国的油画是利玛窦在1601带来的,那时利玛窦向北京的皇帝进献了礼物。李弘祺(Thomas H. C. Lee)在他的书《中国和欧洲:16至18世纪图画与影响》(China and Europe: Image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阐释到,明朝后期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西洋画。尽管没有大师级的作品,传教士们带来了关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绘本,当时在朋友间手手相传(当时主要的基督教信徒在南京和北京)。(2)
那些能够接触到这些西洋画的人们都非常惊讶于画作的写实性——西方的透视技巧和明暗对比。粗略地从“凹/凸”翻译成中文的绘画词语“凹凸画”以三维的角度表述了对之的新奇感。(3)
少数的一些画家,像曾鲸(Zeng Qing),尝试着以他自己的技巧画一些西洋写实的事物,虽然他用的是墨汁,他画的一些肖像看上去就像是镜子里的映像,非常好的抓住了他们的精神和感觉。他的色彩很浓烈。点在那里的眼睛瞳孔就有着动画的效果;尽管脸部都是(画)在纸上或者丝绸上的,但是他们就在怒视、凝视、皱眉或者微笑,忧虑的神情如真人一般。(4)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支持,对西方绘画的批评说,这完全就是数学、技术,仅仅是工匠的工作,或者就像邹一桂(Zou Yigui)所说,
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一,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5)
尽管宫廷画家对其嗤之以鼻,耶稣会教士还是想方设法以西洋绘画的模式,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艺术家,这样他们就能帮助教堂绘画。像游文辉(Yu Wenhui)这样的艺术家,曾经在日本跟随耶稣会教士学习了两年的西洋绘画,后来他创作了一幅利玛窦的肖像画,以及一些其他受欢迎的宗教场景的作品。当时这些画挂在中国的基督教教堂内。(6)
直到17世纪末,由于得到了当时的推崇西方科技的康熙皇帝的支持,西洋绘画在中国得到了大力发展。在画家焦秉贞(Jiao Bingzhen)的努力下,一所教授中西绘画的学校出现了。焦秉贞画了一组水稻种植的图画,推广了西方视角下的绘画技巧。1736年,随着乾隆皇帝设立了清宫画院(Qing Imperial Painting Academy),西洋绘画又得到了一次大发展。清宫画院向那些文人画家教授西洋绘画技巧,让他们把这些技巧带回家乡。(7)
在耶稣会时代的初期,介绍西方绘画有着明显的宗教动机——魔力般的现实绘画在中国赢得了很多教徒的皈依,就像其当初在西方一样。它在17世纪的推广与宣传恰好得到了当时中国皇宫的大力支持。然而,19世纪的“出口画家”引入了交换的多种商业驱动模式。
在澳门、广东以及香港,一些作为雇工的艺术家们,或多或少的在生产用于国外消费的油画——这也是深圳大芬画家村的初期模式。
著名作家范发迪(Fa-ti Fan)博士在他的《清朝在中国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和文化冲撞》(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场景:
根据19世纪30年代的描述,那时在外国工厂邻近的地方有大约30多个出口画的工作室。……这些生意都是家庭式的,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一幅画可能要经过好几个人之手才能完成。一个画匠负责绘出轮廓,另外一个将人物画进去,第三个人则负责画背景之类的。……这些完成的画被成箱的运到欧洲,也被西方的游客当作纪念品带回了家乡。(8)
这些作品主要是包括系列画的风景作品和殖民地风格的日常生活场景画——采茶和丝生产。其他的主题还包括轮船——由英国人推动的风潮和由于他们对轮船制造技术的兴趣。
中国的画家还制作了相当数量的帝王画像或者是圣人画像,这些人像尽管缺少脸部识别特征,通常买家会提供一些他们能识别的道具。(9) 大多数在广东和澳门工作的这些画家,都从一些以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为根据地的欧洲画家那里获取灵感,比如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奥古斯都·博杰尔(Auguste Borge)、威廉姆·普林赛普(William Prinsep)、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查理·威格曼(Charles Wirgman)。但是在中国仍然出现了自己的大师和画家,例如关联昌(廷呱Tingqua),他集合了一大批的助手,在流水线式的工作室内工作,在那里每一个艺术家都只负责风景画的不同部分,正如上面所描述的。
尽管这些交易方式对当时参与其中的画家的生计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它却没有对“现代美术”本身产生影响。艺术史学家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认为,这是由于外国介入到画品交易中的一个相当大的结果。当耶稣会教士努力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进行交换时,涉及出口绘画作品的商人们却并没有这样友好。(10)
土山弯画馆
经历了出口油画的时代之后,中国的耶稣会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存在。
19世纪中叶,上海是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中心。在引入大量西方绘画技巧和为中国学生创立教学设备方面,土山弯画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帮助在中国撒播了现代绘画的种子。
通常,耶稣会是建立孤儿院。1852年在神父范廷佐(Father Joannes Ferrer)的倡议下,土山弯建立了一家工艺培训学校。这些孤儿在此学习木雕工艺、西方油画技巧、印刷技术和染色玻璃生产,这些技艺让他们在后来获得了工作。学校还制作了一些绘画手册;众所周知地成为了中国第一处可以系统教授西方绘画的地方。教学方法包括要求学生复制模特来学习如何准确地在三维透视下再现人形。(11)
尽管这些看上去似乎是任何绘画班的基础要点,对于习惯了国画大致描画人物特点的这些学生而言,这些技巧都是国外的。
当然,在耶稣会活动中仍有动机的存在——通常都是公然的宗教主题和服务于教堂的需求。很多作品都挂在了教堂的墙上和出售给了私人买家。因为他们作品的技术质量,土山弯的画家还是获得了国际的认可。而耶稣会的神父们为这些孤儿们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像徐悲鸿(Xu Beihong)和徐咏青(Xu Yongqing)这样的艺术家,得以在学校获得西方绘画技巧的教育。(12)
留学海外和上海西式美院的增长
一名土山弯画馆的学生周湘(Zhou Xiang),甚至在1911年开设了他自己的绘画学校——第一家西方绘画学校,专门教授为照相馆绘制油画背景。其他的学生开始自学,他们搜集各种他们能找到的材料绘画——那些在沿北京路的旧书店能买的杂志上的广告和肖像。
1912年刘海粟(Liu Haisu)——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目前在上海的虹桥地区仍有惨淡经营的同名博物馆),开设了图画专修班,后来该校在1915年成为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Shanghai Painting and Art Institute),那是他年仅17岁。刘海粟不仅仅因他有力的笔触出名,而且还因在学校内开展裸体绘画和写生课而获得声誉。第一名模特是一位15岁的男孩,不过后来刘海粟为学生们找到了一位俄罗斯模特。他的这一举动招来了当地军阀的恐慌和来自教堂的众多批评。人体绘画的观念说明,对于仍然保守的后清朝时代的观念,这太超前了。而刘海粟的使命因为蒋介石(Chiang Kai-shek)的到来以及那些提倡对艺术和教育保持更开放的现代观念的民族主义者而获得了解救。
在上海其他学校也陆续开设起来。比如说1914年,乌始光(Wu Shikuang)的绘画研究院(Institute of Pictorial Art);在徐家汇,1919年时,通过震旦大学(Université Aurore)耶稣会仍然在教授法国风景绘画技巧。
以长居上海的艺评人、编剧赵川(Zhao Chuna)说,上海的外国因素实际上在这早期的中西方艺术对话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以上海为例,法国艺术有着重要影响。法租界产生了强烈的文化碰撞;其他的租界区商业性更浓。在19世纪30年代,很多的艺术家前往法国和比利时学习。”(13) 法租界是一小部分立体派、野兽派和象征主义知识分子的家。在20世纪30年代,法租界里也有一批艺术类杂志,比如《艺术旬刊》、《艺风》,以及通过翻译、最有效帮助传播对超现实主义理解的杂志《艺术》。(14)
通过海外交流,尽管很多学生前往法国或者日本(学习艺术),少数中国学生因为家庭移民而前往美国学习艺术。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那些美国的中国艺术家才发挥出更多更重要的艺术影响力。这样大规模的外流实际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并且由于战争在欧洲的结束、以及强调需要打开眼界的五四运动国际主义思想而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北京的新机构和宣言
北京也是在引进西画方面非常有影响力的口岸之一,蔡元培等人物在提供负担得起的艺术教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出名的教育家和学者,蔡元培在1918年为那些无法负担绘画费用的学生开设了北大画法研究会(After Hours Painting Research Society)。后来到1920年,北京大学在他的领导下设立了平民夜校(Common People’s Night School)。
那时的北京吸引了一批外国艺术家,比如法国艺术家克劳多(Andrée Claudot),他后来也受到中国国画的影响;还是有捷克的艺术家齐蒂儿(Vojtech Chytil),他帮助交流艺术家Wang Meng和Sun Shida前往布拉格艺术学院(Prague Academy of Art)学习。
但由于政治风潮进入北京,由于他们“激进”的观念50位教授而被捕,林风眠(Lin Fengmian)和其他的艺术家纷纷逃离到其他地方。就在他们离别之前的1927年5月,他们在北京艺术大会上聚集,在这次大会上他们宣布了对新艺术哲学的信仰,提出下面的宣言:
打倒模仿的传统艺术!
打倒贵族的少数人独享的艺术!
打倒非民间的离开民众的艺术!
提倡创造的代表时代的艺术!
提倡民间的表现十字街头的艺术!(15)
相当有趣的是,让当时的民众真正地接受这样的艺术形式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不过在上海对西洋画的兴趣依旧在增长。
宣言仍然显示出那些传统精英们对接触艺术的强烈拒绝,传统的学习方式中艺术家的大多数被限制在仅临摹大师作品,而新艺术却提倡对现实生活的艰苦进行真实的反映。这与传统的国画哲学有着尖锐的对比,传统的国画哲学宣扬的是,我们应该通过对自然界理想化的描绘,引申出一个道德和哲学的理想。
南方的中国学校
离开北京后,1928年,吴法鼎(Wu Fading)和林风眠(Lin Fengmian)与蔡元培(Cai Yuanpei)一起开办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National Hangzhou Arts Academy),这也是在杭州的中国美院(CAA)的前身。不久就在包括苏州和南京在内的许多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里出现了艺术学校。
曾在日本学习绘画的艺术家任瑞尧(Ren Ruiyao)、胡根天(Hu Gentian)以及在旧金山学习绘画的冯钢百(Feng Gangbai),他们的归来也让广东展开了西洋绘画的历史。他们共同组织了赤社(the Red society)——一个除了名字以外与共产党毫无联系的美术团体,通常只是创作一些温和的肖像画及风景画。其他一些小的组织渐渐在福建、成都、重庆和无锡开始出现。(16)
早期的日本影响
在这一时期,通过在中国的日本老师、学生前往日本(在20世纪初期有超过1000人前往那里学习)和翻译日语版的关于西方美术的书籍,西洋绘画风格的主要影响都是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的。这类翻译的书籍中甚至包括了像马林内谛(F.T.Marinetti)所著的《未来派宣言书》(Future Manifesto)全本。(17)
上海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聚集在内山书店(Uchiyama Shoten bookstore)交换现代派的观点。(18) 书店的主人内山完造(Uchiyama Kanzo)是中日文化交流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书店坐落在四川路上,提供特定的书籍,包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有关西方法律的书、日文版的西方文学书籍还有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书店的大多数中国客人多数都曾经在日本生活过,这里也变成了一个类似的文学沙龙,内山先生经常会组织一些中日作家间的聚会。(19)
内山书店几乎就是鲁迅的第二个家,他每天都去。内山书店还是那些政治敏感邮件的留局待取的地方,内山先生常常为那些从秘密警察那里逃离出来的作家提供庇护。(20)
1902年,当西方绘画技巧被纳入从初级小学至大学的学校课程中时,大量的日本教师被带入中国进行帮助和指导。(21) 但是在五四运动期间,许多学生通过发表政治声明而远离了日本的艺术家、老师以及机构。(22)
尽管出现了这次的反日声明,日本人还是对后来的中国木刻运动产生了影响。鲁迅(Lun Xun)从上海邀请了13名学生跟随日本艺术家内山嘉吉(Uchiyama Kakichi)学习木刻技术。通过他收集的日本和俄国的木刻作品,鲁迅传播了媒体的意识;随着日本的侵略,内山嘉吉的中国学徒们把他们的技艺传遍中国,一些到了延安(Yan’an)和其他革命活跃地区工作。(23)
对他们而言,木刻的民间粗糙感与工人阶级要达到的共产主义目标是吻合的,同时它也很便宜和易于快速宣传的制作。木刻画上的具有社会意识主题的事物、强烈的绘画风格和吸引人的剧情,比起那些在宣传海报上可以找到的更现实意识形态的形象,有着更大的作用。
早期的苏联影响
尽管意识形态已经改变,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与苏联的交流依然对采用现实主义为主导模式的中国当代艺术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出现过一个被称为“流浪者”(Wanderers)(又被称作“流动展览艺术协会”(Society for Itinerant Art Exhibitions))的团体。从方式到主题,他们都会产生巨大的碰撞。这一艺术家们漫步在乡村旷野,描绘着每日生活的场景(特别是苦难的)。这一想法恰巧与毛泽东关于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思想不谋而合,与木刻艺术家的行动同时进行。
安雅兰(Julie F. Andrews)描述了第一个官方交流被派到中国来的苏联艺术家——流浪者康斯坦丁·马克西莫夫(Konstantin Maksimov)。艺术家江丰(Jian Feng)是这样称赞这一活动的:
马克西莫夫同志来到中国,使我们有机会直接地、有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艺术经验。我们相信在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指导下,不论在我们的美术教育事业上,或在油画师资的培养上,将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宝贵的贡献。(24)
要得以进入马克西莫夫培训班的竞争是激烈的,那些做出裁减决定的人让它实现,让这些得以接受学习的人们回到家时能够在艺术机构中找到自己永久的位置。
马克西莫夫的绘画并不像我们会联系起来的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海报艺术般耀眼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含有大量色块的更富有表现力的风格。他的这一风格同样也被在列宁格勒(Leningrad)列宾美术学院(Repin Art Academy)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吸收。马克西莫夫所留下的不仅仅是对跟随他学习的学生产生影响,而是整个中国艺术界产生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他对颜色的使用、他要求学生应该专攻某一特定题材的观点、他对典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历史绘画复杂构成的介绍和他关于教学的方法,都为现在的中国艺术学生们能获得的技艺水平做出了贡献。(25)
70、80年代有限信息的交流
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当中国的艺术王国开始自由化时,曾经出现了一次从立体主义、到野兽派、到印象派、包括每一样事物在内的早期现代绘画不同形式的繁盛。但是,尽管再次渴求对西方绘画风格的探索,获得信息的方法仍然集中在相当少的一些渠道。
文化杂志《上海文化》的艺术评论人和编辑吴亮(Wu Liang)是这样给我们描述场景的,“一个原因是,在那个年代交流生非常少,大多数去西方的参观者都是一些跟随政府的官方短期旅行去的——他们宁愿去卢浮宫(Louvre),然后回来能够写下他们所看到的。”
太少机会能够看到当代艺术的作品,许多艺术家不得不依赖于通常看到的低劣的复制品——粗糙的细节和失真的颜色。吴亮认为,“(那时)我看到过印象主义的复制品,当我去了美国之后看到莫奈(Monet)和梵高(Van Gogh)的原作时,我意识到之前我所看到的复制品都只是简单的复制品。要看技术、笔触和颜色之间的关系你必须看到原作。”(26)
坐在他位于巨鹿路常春藤作协的办公室里,吴亮讲述了关于陈丹青(Chen Danqing)的故事,那时他碰巧在扑克牌的背面发现了一幅女人的绘画,于是他画了自己的版本。尽管一开始还相当满足最后的结果,当后来他在一次国外的旅行中亲眼看到同样风格的原始作品时,他感到相当的泄气。吴亮说,他当时说到:“我不能画了。这些都画的太好了,我还能画什么呢?”(27)
去国外的机会仍然相当的少,照相机和照片还是相当的贵,艺术书籍那时总是相当火热的商品,赵川在他的文章《上海往事:20世纪上海激进主义艺术》这样写道。(28)
余友函(Yu Youhan)借了一本郁特里洛(Maurice Utrillo)的画册给了丁乙(Ding Yi)。因为才认识,书就只借一天。那本画册是通过很多人之手辗转从日本带过来,这样的书当时只有上海美协有一套。丁乙拿了画册在食堂里通宵临摹,画了十张八开的。画面中的单纯结构,成了他后来画《十示》(Appearance of Crosses)系列的出发点。
赵川提到,上海美术家协会是当时少数几个地方之一,一是能看到很好目录的收集,并且能当作一个会场为朋友间互相交换材料服务。
那个时候艺术家们都急切地想获得关于西方艺术的信息。赵川说,“70年代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仅对教授们开放,所以像张建君(Zhang Jianjun)这样的艺术家不得不要求特许才能进入。教授们也会让他们进去,然后锁上门,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他们在图书馆里面了。”(29)
80年代杂志提供了西方艺术形象的通道
在(20世纪)80年代像《美术译丛》、《世界艺术》和《雄狮美术》等也扩大了获取西方艺术的渠道,虽然复制品常常有一些需要改进,吴亮还提到,“来自台湾的《雄狮美术》有着最好的复制品,因为台湾的印刷技术比那时中国的要好很多。而且对台湾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不会有某种偏见或者都是同一个性。因为台湾人已经与国外进行过很多交流,他们不会对某些来自国外的新事物大惊小怪,他们对这些事物不再那么激动。”(30)
这里吴亮指出了筛选的问题,有关于西方艺术的信息以不同的方式被呈现——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非常的异质,但还是要为观众写下来,因为他们并不是非常熟悉这些材料。
现场直播:80年代个人之间的有限联系
当20世纪初,上海用“欢迎林校长”的横幅欢迎林风眠时,宣布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对他的任命。而80年代从国外回来的艺术家们不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备受欢迎了。吴亮说,“在国民党时代,我们感到必须要学习,因为我们的国家落后。刘海粟回来以后开始建校——他们有很多的自由。而80年代的情况是不同的。在80年代,他们没有回来。现在这些海归(returnees)回来是因为某些特殊政策或者是能获得某些特殊待遇。”(31)
直到2000年的中后期,我们才开始看到曾经在国外工作的艺术家回归,但是只有少部分以教书为职业。2008年徐冰(Xu Bing)出任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一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2000年陈丹青回国后不遗余力地开始在清华授课,但是在2005年辞去了工作。引用(他的)原话是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巨大失望,因为要求艺术类的学生必须通过英语考试。
其他的归国者,比如1993年回国的艾未未,为年轻艺术家们提供鼓励,向在其不断扩大的工作室里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艺术家们传递想法(比如艺术的能力可以制造政治声明),并(推向)整个社会。

Jean-Michelle Basquiat, In Italian, 1983. Acrylic, oil paintstick, and marker on canvas mounted on wood supports, two panels.
90年代开始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同样也提供了帮助,不仅仅是西方艺术,而且还有跟实际的资源,赵川(Zhao Chuan)提到,“这个体系是一个西方的体系、西方的策展人、西方的画廊;通过他们的宣传,他们帮助我们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体系。大多数的这些信息都来自国外。我们开始学习,通过这个如何设置、如何让其生效。在90年代,我们总是要看目录、和外国的策展人不停地交流、不断地看幻灯、和学习如何加入到中国当代艺术的行列中去。” (32)
像戴汉志(Hans Van Dijk)这样的策展人——在艺术家圈子里亲切地被称为“老汉斯”(lao hanse)——广泛地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第一个重要的策展人和艺评人。在90年代早期,戴汉志(Van Dijk)给艺术家的作品提出自己的建议,在自己北京自己的家中举办小型的展览。 其他在早期有影响的策展人还包括马田(Jean-Hubert Martin),他在1989年策划的展览“大地魔术师”(Les Magicients de La Terre)是第一个在国外以中国当代艺术家为主的大型展览;还有在1999年通过介绍蔡国强(Cai Guoqiang)(和他的作品《威尼斯收租院》(Rent Collection Courtyard))到威尼斯双年展将这种影响扩大的赫拉德·史泽曼(Harald Szeemann)。
接下来
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聚焦于信息传递的方式——涉及到的人、出版物和机构,以及信息是如何被传播的。在第二篇文章中,我们将更多地探讨从70年代以来这些影响的美学效应——将涵盖里程碑式的西方艺术展览和人物,像对中国当代艺术留下印迹(孔斯的情况是个污点)的塔皮埃斯(Tapies)、罗森博格(Rauschenberg)和孔斯(Koons)等。
(1) 相反的,中国艺术在西方的影响同样也是一个有效的话题,不过将不会在这篇文章中涉及。
(2) 李弘祺《中国与欧洲:16至18世纪图画与影响》,第254页,香港中文大学,香港,1991年。(Thomas H. C.Lee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1991,p254)
(3) 同上,第255页。
(4) 同上,第257-28页。
(5) 苏利文《东西方美术的交流》,加州大学出版社伯克利分校,1989年,第80页。(Michael Sullivan 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9)
(6) 孟德卫《中西方的伟大相遇 1500-1800》,第42页。(David Mungello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
(7) John W. O’Malley, S. J. Gauvin Alexander Bailey, Steven J. Harris, and T. Frank Kennedy, 《耶稣会教士卷二:文化、科学和艺术,1540-1773》 (The Jesuits II: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多伦多,2006年,第263页。
(8)《清朝在中国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和文化冲撞》,哈佛大学,美国,2004年,第48页。(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USA, 2004.)
(9) 克里斯蒂娜·贝尔德《利物浦中国商人》,第110页。(Christina Baird Liverpool China traders)
(10) 苏利文,第82页。
(11) 梁庄爱伦《出售幸福:20世纪早期的月份牌和视觉文化》,第63页。(Ellen Johnston Laing Selling Happiness: Calendar posters and visual culture in early-twentieth…)
(12) 苏利文《20世纪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第30、42页。(Michael Sullivan Art and Artist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3) 来自Rebecca Catching和赵川之间的一次采访。
(14) 苏利文《20世纪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第52页。(Michael Sullivan Art and Artist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5) 苏利文《20世纪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第44页。(Michael Sullivan Art and Artist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6) 同上,第45-52页。
(17) “Points of Encounter – a Timeline to be Completed,” Defne Ayas,with contributions by Leo Xu, Francesca Tarocco and Matthieu Borysevicz,
(18) 同上。
(19) 克里斯托夫·T.凯维尼《超越画笔交流:中日战争期间的文化交流》,第28-30页。(Christonpher T. Keaveney Beyond Brushtalk:Sino-Japanese literary exchange in the Interwar Period.)
(20) 刘禾《跨语言实践——文学、民族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年,第418页。(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
(21) 苏利文《20世纪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第27页。(Michael Sullivan Art and Artist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2) 苏利文《20世纪的中国艺术》,第46页。(Michael Sullivan Chinese Art in the 20th Century)
(23) 安雅兰、沈揆一《中国五千年》,展览文字来源于http://kaladarshan.arts.ohio-state.edu/Exhibitions/5000YearsText.html (Julia F. Andrews and Kuiyi Shen China 5000 Years.)
(24) 安雅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绘画与政治,1949-1979》,第152页。(Julia Frances Andrews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25) 同上,第155页。
(26)
(27) 来自于2010年8月,Rebecca Catching对吴亮的一次采访。
(28) 赵川《上海往事》,刊载《上海文化》2009年,秋季增刊,第86页。
(29) 2010年8月,Rebecca Catching对吴亮的专访。
(30) 2010年8月,Rebecca Catching对吴亮的专访。
(31) 同上。
(32) 同上